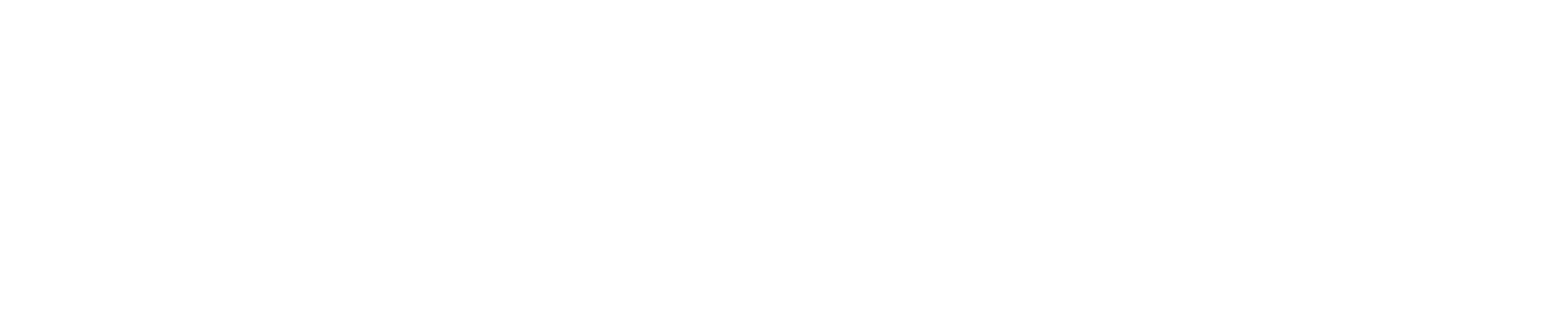
紀法講堂丨賄賂案件中“中間人”行為性質分析
實踐中,存在“中間人”的行受賄犯罪事實較為常見,有的“中間人”深度參與行受賄過程,甚至從中截取賄賂,對于這種情形如何準確評價“中間人”的行為性質,容易存在不同認識,筆者結合一起案例進行分析。
李某,A區分管城建工作的副區長。歐某,A區某公司職員,與李某系發小,兩人一直交往密切,歐某多次請托李某利用職權辦事,李某均有求必應。劉某,某建筑工程公司實際控制人。2018年1月,劉某知道歐某與李某關系密切后,遂向歐某提出請李某幫助承攬A區的某土方工程,承諾給予好處費。2018年2月,歐某向李某轉達了劉某的請托,李某同意并與歐某商定索要120萬元好處費二人均分。后歐某告知劉某工程可以干但需150萬元好處費,劉某答應。在李某幫助下,劉某所在公司承攬了某土方工程。2018年6月,劉某將150萬元現金交給歐某,歐某自留90萬元,將剩余60萬元交給李某并表示這是商定好的一半好處費,李某收下。
本案中,對李某、歐某行為性質如何認定,存在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歐某與李某共謀,利用李某職務上的便利幫助劉某承攬工程并收取好處費,二人構成受賄罪共犯,應當以歐某收受劉某的全部150萬元認定共同受賄數額,歐某與李某分別獲得多少是受賄人內部對贓款的分配問題,不影響共同受賄數額150萬元的認定。第二種意見認為,歐某與李某構成受賄罪共同犯罪,但共同受賄數額應以二人合意的120萬元認定,歐某私自多要的30萬元不在李某的犯意之中,對該30萬元應認定歐某單獨構成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筆者同意第二種意見。
首先,結合主觀方面和客觀行為認定罪名。從外在行為看,許多情況下,正是因為“中間人”的居間聯絡才促成了行受賄犯罪的達成,其既幫助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財物,亦幫助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但從犯意聯絡看,不同案件里,“中間人”與請托人、國家工作人員間的聯絡存在明顯差異,比如,有幫助請托人謀取不正當利益并給予國家工作人員財物的,有幫助國家工作人員轉達承諾并索取或收受財物的,還有獨立于雙方利益僅收取居間介紹費的。在“中間人”與國家工作人員構成共同受賄的案件中,“中間人”依附于國家工作人員一方,主觀上具有共同收受賄賂的意思聯絡;客觀上“中間人”有幫助國家工作人員收受賄賂的行為,不僅限于轉達意思,而且積極參與索取或收受財物,并存在共同占有等行為。“兩高”《關于辦理受賄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規定,“特定關系人以外的其他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謀,由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托人謀取利益,收受請托人財物后雙方共同占有的,以受賄罪的共犯論處”。本案中,歐某與李某共謀幫助劉某承攬某土方工程,并就收受及分配劉某給予的好處費達成一致,歐某后續還實施了幫助李某收受好處費并分贓的行為,應認定歐某與李某構成受賄罪共犯。
其次,結合共謀內容及實際收送情況認定共同犯罪數額。存在“中間人”的行受賄案件中,請托人與國家工作人員通常不直接接觸,賄款一般在請托人與“中間人”之間交接,而“中間人”基于趨利性,常出現多收賄款的情況,如此易產生共同受賄人對受賄數額的主觀認識與請托人實際給予的金錢數額不一致的情況。筆者認為,根據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當“中間人”未告知國家工作人員多收受錢款時,國家工作人員主觀上對“中間人”多收錢款是不明知的,“中間人”多收的數額超過共謀的故意范圍,不宜認定為共同受賄數額。本案中,歐某與李某商議幫助劉某承攬某土方工程、收受120萬元好處費后二人均分。但實際上,歐某向劉某索要150萬元,超出的30萬元歐某并未事先或事后告知李某,不在李某的認知范圍之內,超出了二人的共謀內容,不宜認定為共同受賄數額,故李某與歐某共同受賄數額應認定為120萬元。
再次,結合各方對截賄款的主觀認知判斷“中間人”截賄行為的性質。通常情形下,“中間人”截取賄款,無法證明國家工作人員明知的,因二人主觀上沒有共同占有賄款的故意,不宜認定為共同受賄數額。但“中間人”主觀上明知確系利用其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關系為請托人謀取了利益并截取了賄款,而請托人對該賄款系權力對價(即系利用“中間人”與國家工作人員的密切關系幫助自己謀利的對價)具有主觀明知,其對錢款在“中間人”與國家工作人員之間如何分配持放任態度。因此,這種情形下,“中間人”截賄的行為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本案中,歐某瞞著李某多要了30萬元,從主觀上看,歐某明知這是利用與李某的密切關系幫助劉某承攬土方工程的對價,從客觀上看,歐某實施了利用李某的職務便利幫助劉某承攬土方工程并收受30萬元的行為,歐某的行為符合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構成要件,應認定歐某利用影響力受賄30萬元。